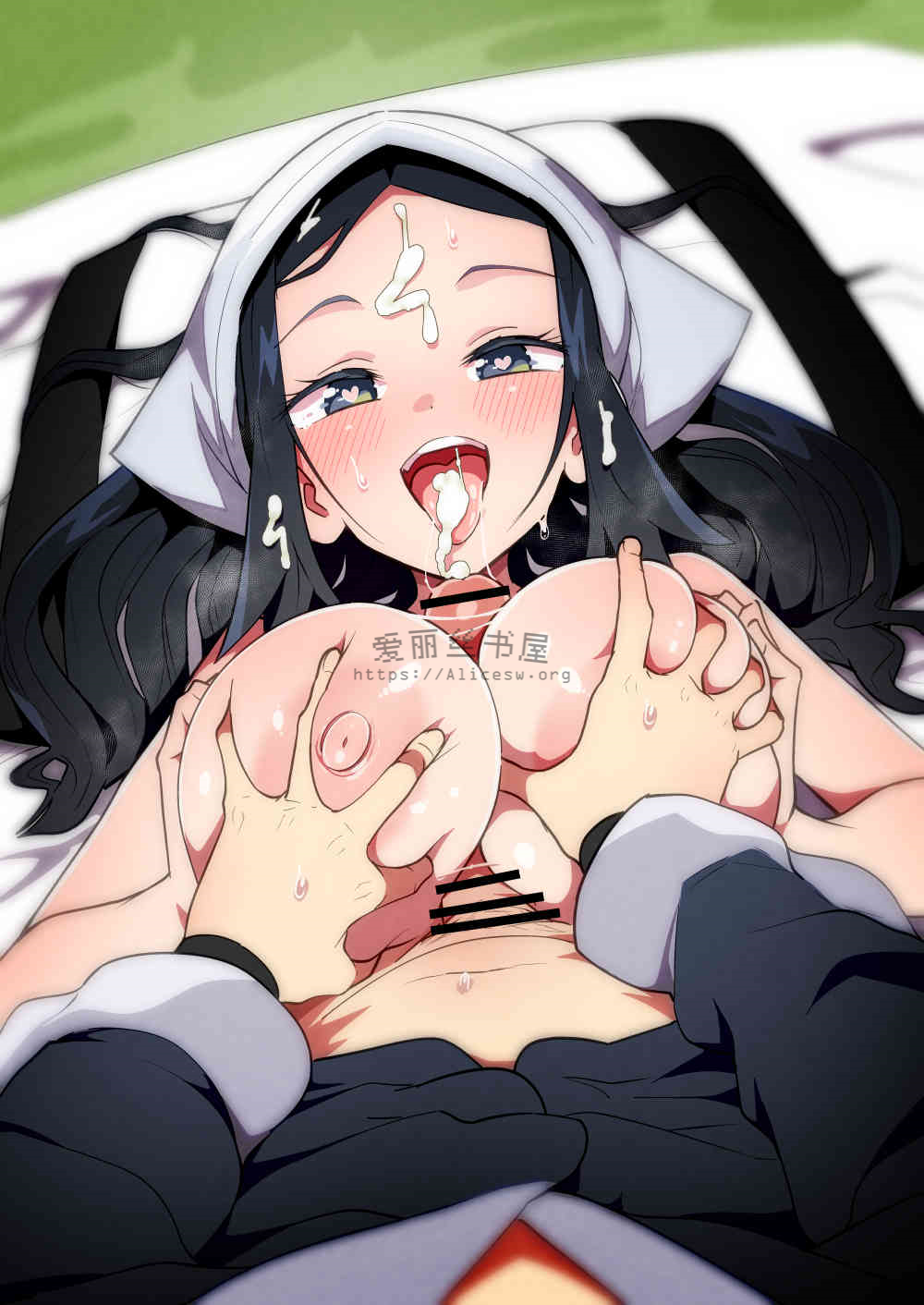重樱神子的殿前杖责
重樱神子的殿前杖责
“山风厉吹花易散,和琴雅乐,岂可复闻乎。”
残烛将熄,透光的敷居下,和室里跪坐在灯芯草席上的御子长门正沐浴着熹微晨光,阖眸祷告。
如瀑般的乌黑长发自然柔顺的披散至肩头,量身缝制的襦袢緋袴在跪坐的姿势下勾勒出浑圆紧致的臀部,因侍神巫女装束的矜持显得色而不淫,白皙如脂玉的肌肤在柔光中仿佛覆上了一层神性的晕染,身材娇小的狐耳少女却令人仰之弥高,她不愧为天钿神宫的大宫司,凭天宇受卖命的恩赐,仅是幼女之姿,举手投足之间却尽透出一股难掩的贵气和威严,即便是身陷囹圄也能坐怀不乱。
长门将长阖的眼眸睁开一条缝隙,瞥了一眼面前桌案上一箸未动的食盒,里面的米饭已经变得冷硬,味增汤也只小抿过一口,里面加了难得的蟹味增,至少这群软禁自己的土一揆还懂得礼遇,但这样幽禁于外界的生活却令长门日益焦躁不安,那些抢占了神社的土一揆从始至终不肯对自己透漏半点关于三方圆的消息,在此之前她只知道三笠大人驰援三河城的大军被凉月所集结的倾巢之兵大败,现在已经退守淞城,而凉月军则得以继续向西高歌猛进,三笠大人在东线战场的形式如履薄冰,也正因如此,得知三笠兵败的后方国人众才敢收买百姓发动一揆,而作为助三笠大人镇守后方,推行吏治的天钿神宫宫司,自己自然在他们所要擒拿的三笠党羽之列,甚至能排上前三甲也说不定。
想到这些烦心事,连心跳也跟着鼓动起来,未穿足袋的裸足不安的交叠在一起,脚趾也因为紧张而蜷缩着,如果有人得幸从背后一睹这位御子身姿的话,绝对会被那双白皙中透着淡淡粉红,一眼便知是被娇生惯养出来的贵女才有的小脚丫吸引住,如同璞玉般嫩滑的脚板肉感十足,就连蜷起的脚趾也带着一股调皮的可爱,就算是清心寡欲的僧侣也难免会感叹,这样的孩子生于污浊的尘世,实在是令人于心不忍。
实际上,诸如此类的话长门从小已经听过无数遍,但相比起自己眼下可怜的处境,她的担忧已然在千里之外,如果三笠大人一败涂地,那么自己也……
‘唰——’
敷居的滑门被粗鲁的推开,灼目的日光照进和室,将晦暗的角落涤荡殆尽,天空高远而晴朗,湛蓝的甚至有些承受不住,流云仿佛翻腾的白浪,一遍遍洗刷着苍穹。
长门下意识的抬袖遮掩刺眼炎阳,手腕却被另一只粗粝的大手在半空中擒住,长门一阵错愕,耳朵如受惊的小兽般猛地竖起,她半眯起眼睛试图看清楚面对对自己如此无礼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回应她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啪!”
的一声,力道之大几乎让长门扭过头去,与灼烧般的痛楚一同蔓延到脸颊上的还有没齿难忘的屈辱,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当自己是块易碎的美玉般呵护,受过最重的惩罚也不过是因为过于顽皮被老宫司按在大腿上,隔着緋袴打几下屁股,可只要喊疼的童音一响,或是幼女的眼角用力挤出几滴泪花来,老宫司就会立即停手,再把自己抱在怀里顺发安抚。
巴掌招呼在娇嫩脸蛋上的锐痛,哪怕是倾城町里……不,就算是冈场所里的卖春妇也鲜少受如此折辱!
愤恨的情绪蔓延到四肢百骸,不顾晴日灼目,长门睁大了眼睛怒视着非礼自己的恶徒,却发现眼前正得意哂笑的家伙居然是这几日一直在为自己送餐的土一揆,此人乃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跟自己所见过的百姓布衣们一样,永远都伛偻着身形,半饥半饱的样子,只是因为送餐时谦和恭敬的态度才让自己记住了他的样貌而已。
但平时看起来本分的土一揆现在却对自己出手狠厉,很难想象那只有些枯瘦的手居然可以打得这么疼……
“给我起来!你这反贼三笠的走狗!”
土一揆攥紧了长门的手腕粗暴的拉扯着,迫使她站起身来,与成年人的身高差让此刻被提起一条手臂的长门像极了尖钩上的活鱼,痛苦的忸怩着身体。
“你说什么……反贼?……”
长门吃疼的咬紧银牙,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她还是从土一揆的话里听见了些端倪,即便这些乌合之众举兵一揆,也是断然不敢直呼三笠大人为‘反贼’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会让三笠大人和自己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危险的噩耗。
“给我一字一句的听清楚了,你这只狗仗人势的小狐狸——”
跋扈的土一揆撇下了长门的手腕,却又一把揪住她的耳朵,冲着狐耳内的一团绒毛吐出一口浊气,长门下意识的打了个激灵,这样楚楚可怜的表现却令男人很是满意
“三方圆一战,凉月大人天下归心,现在就连出云大将军也放弃了三笠,将军已经在妙显城颁布了讨逆檄文,发兵截击三笠的残众,于势于理,三笠军都已经完蛋了,你也会和她一样!”
仿佛牵引着木偶的提线忽然被斩断了一般,长门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下瘫了一截,险些就要跪在地上,在精神短暂的涣散之后,她强撑起最后一点理智,用近乎是哭腔的颤音开口问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似乎是小狐狸的啜嗫和介乎于恨与辈之间那惹人怜爱的神情终于触动了土一揆某根欲念的弦线,男人并没有作答,而是一脚踢翻了盛放着餐盒的桌案,米、汤和碗筷狼藉的洒落在灯芯草席上……
“浪费食粮的坏孩子,就该这么受罚!”
不顾长门怎样的踢打挣扎,土一揆不紧不慢的坐下,只手如钳般桎梏住长门的细腰将她强行按在自己的大腿上,摆出如同做了错事的小孩子被父母脱了裤子打光屁股一样的姿势,像长门这样尊为神宫宫司的贵女,他一辈子都碰触碰到过一片衣角,如今却能隔着绫罗薄纱般的緋袴肆意揉捏那包裹在下面的,软嫩圆润的小屁股,不,完全可以做的更加狂妄一些。
“本来留着你就只是作为要挟三笠的筹码,现在你家主子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作为战利品,你猜猜自己会被怎么处置?”
土一揆的诘问令长门语塞,一字一句像是有千针刺心,咬紧的银牙间发出愤恨的嘶吼声,小手攥紧成拳拼命地在草席上捶打,身体也不停地忸怩挣扎,但这些声音在土一揆听来却像被捕兽夹困住的狐狸向猎人无意义的邪呲一样,除了令他更想驯服这位娇小可爱的贵女之外再无其他用处。
粗粝的巴掌高高扬起,隔着緋袴在长门的小屁股上落下了第一掌,一声可怖的闷响给一瓣臀肉覆上一层清晰的钝痛,长门下意识的喊叫出声,身体也不由自主的绷直成一线,这倒是正顺了土一揆的心思,在一次呼吸的停歇之后第二掌也呼啸而至,土一揆们多是乡野的农户出身,那些久经繁重农务,早已经裹上一层老茧的巴掌其中所蕴含的力道根本不是她一个自由锦衣玉新的小丫头所能承受的,往年逢初午稻荷祭,自己往那些乡野神社巡幸时,也曾见过乡下的粗人是怎么打女孩屁股的,不过是被达人脱了裤子夹拎在腰间用巴掌扇光屁股,但几巴掌下去那两瓣原本白净的臀蛋就会变成掌痕交织的桃红色……
长门一直不信,光是用手来打屁股能有多疼?直到这份疼真打进了自己的娇贵嫩肉里,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都那么怕‘屁股开花’,当疼痛蔓延到整副臀面时,那感觉就真的像屁股蛋要裂开一样,跟老宫司那玩笑般的拍打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难道农夫家的女儿从小就受这种苦?隔着緋袴就已经疼成这样的话,被打光屁股又是什么滋味?
长门又难以抑制的悲天悯人起来,可御子的慈悲心刚要荡漾起来,第三巴掌就不偏不倚的往臀峰处落下,力道之大即便隔着緋袴也能看见长门的左瓣臀蛋生生凹下去一块,痛感在臀峰处爆炸来开,像掀起了一阵强浪瞬间席卷了余下的臀肉,长门惨叫一声,原本因为疼痛而并在一起的一对裸足也顾不上什么矜持,条件反射似的抬起来试图掩住屁股,可这突兀出来的一双玉足又转瞬间成了土一揆亵玩的目标,男人用刚打过长门屁股的手一把抓住一只脚踝,粗粝的指腹贪婪的一遍又一遍从足跟一直摩挲到脚心,指腹所触是嫩如豆腐的脚心,目光所及是白如璞玉的足肉,白里透红的肉色哪怕是铁石人见了也会生起怜爱之情,幼女的小脚丫一旦把玩起来,相比风流万种的遊女也毫不逊色。
可怜的长门只得憋住笑意蜷起脚趾,到忍耐的临界点才终于破口怒骂,但因为混杂着的笑声而显得气势丧尽。
“噗……!混账!嘻……不准再…嘻嘻,再玩弄吾的脚了……”
幼女的娇嗔令土一揆的手法更加放肆起来,在用力搓揉了两下足窝之后便又把玩弄的重心转移到长门的小屁股上,男人毫无忌惮的掀开一直包裹着幼女娇臀緋袴,果不其然这只小狐狸矜持的巫女装束下是无寸缕遮掩的真空,长门只觉得臀峰一凉,紧接着便因光屁股让这非礼自己的男人彻底看了个通透而羞耻的面红耳赤,但从土一揆视角来看,仿佛被晚霞印染的红臀加上紧致的臀峰,红彤彤热乎乎的两块肉垫在被抽打上色后在显得更加饱满,简直比任何珍馐都要诱人。
土一揆伸手握住一瓣娇臀,长门的两片屁股蛋终于从紧绷的状态变成了顺从的柔软,被汗津津的手掌揉捏时会像棉花糖一样粘糯在掌心里,男人轻扇了下长门的裸臀臀峰便掀起了一层臀浪涟漪,诱惑的蜜桃臀在土一揆的拍打之下仿佛软嫩的奶冻一样颤抖弹跳,极佳的手感仿佛是非固体一般软嫩,轻轻抓握便会有臀肉自指缝中溢出……
“不要…不要了……好难受!”
依旧趴在男人腿上无法做出任何反抗的长门只能无助的发出悲鸣,但将她视为玩物的土一揆断然不会在乎她的感受,甚至在长门忸怩的太过厉害时还会直接揪起长门大腿内侧的一块嫩肉以示惩戒,这一招对小孩子格外奏效,长门的呜咽声像是直接噎在了喉咙里,只要她的声音稍微大一点,掐紧大腿内侧嫩肉的力道就要加大一分,在领教过几次钻心的皮肉之苦后,长门终于不再死命的尖叫悲鸣,转而是用婉转悦耳,带着楚楚哭腔的童音向男人低声下气的求饶,甚至会主动翘起屁股求他不要再掐自己的大腿……
沉浸在调教幼女御子的欢愉中的土一揆没有意识到从自己身后闪出的另两个身影,直到驻足观瞧的其中一人用命令的口吻开腔道。
“别再玩了!我们要尽快押走这小丫头,别让国人众等急了。”
来者是国人众手下的皂隶,比起草莽出身的土一揆,他们更有跋扈的资本。
土一揆发狠的捏了捏长门的小屁股,虽然心有不甘,但国人众的命令他不敢不从,何况是马上又要有好戏可看?既然三笠逆贼败局已定,国人众们自然也没有再礼遇这只小狐狸的理由了,至于他们的手段,自己则是心知肚明的。
才不过被玩弄羞辱了几刻钟,对长门而言却比漫长的初午祭更加难熬,但休息的时间却是奢望,他们将她凌空拎起,扔出敷居,推搡着幼女娇小的身躯向神宫正殿走去……
就连一双木屐都不被允许穿戴,长门只好赤着脚一步步踏在碎石小径上,一双白嫩敏感的脚丫子被硌的生疼,以至于步伐都难免的踉跄起来,原本熟悉的神宫路径此刻走来却是如此多舛。
穿过瓦宇林立的别宫社殿,景色变得豁然开朗,晚秋的太阳就像一颗冰粒子,无论如何也温暖不了凉意渗骨的地面,落叶于风中飘转零落,秋风带着凉意游走,草木窸窣摇曳,昭示了风的足迹。
长门注意到大不同于往日的沿途景象,昔日的神舆、彩车、虔诚的香客们全都不见,只剩下空旷的宫阙和囚笼般的四壁,她从未觉得天钿神宫如此陌生,如此冷落,在国人众们鸠占鹊巢接管神宫之后,香客们自然是不再敢来的,至于神宫中的其他巫女,长门甚至不敢去想象她们的命运,她们被安置在何处,生死如何一概不知,但比起自己,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有利用价值的女孩们后续早就承受了不止一轮的非人折磨吧……
江风和陆奥,两个人的身影在长门眼前挥之不去,她攥紧了发凉的指尖,只能在心中一遍遍的乞求凭天宇受卖命可以发发慈悲,成为侍神御子的数年来,她从没向神祇索求过馈赠,但眼下她愿意用攒下的所有虔诚让那两个人相安无事。
但凭天宇受卖命并没有回应自己,长门恍惚的环顾四周,神宫依旧寂静的可怕,一丝神谕也未尝窥见。
冻得通红的裸足踏尽一片枯枝败叶,发出簌簌的干涩之音,再迈出一步时,脚下的石子小径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冷石地砖,每踩上一块都是凉意彻骨,长门只觉得脚趾都变得难以屈伸,但只要自己的步子稍微迈的慢了一点,身后的皂隶便会厉声呵斥,像驱赶着家畜一样逼她继续赶路。
神宫主殿已经近在咫尺,庭院里的人声也逐渐嘈杂起来,一路上神情恍惚的长门这才注意到主殿的两侧檐荫下已经站满了人,从穿着上分辨,无外乎是国人众和土一揆的头目们,其中为首的家伙华服佩刀,俨然是国人众的领袖,那人正站在主殿中央,十二层阶之上,正好可以低头俯视自己,眼神中尽显玩味与轻蔑。
但比起傲慢的恶徒,能够让长门心惊肉跳的却是放置在主殿庭院中央的物什——一张木质的春凳,大概目视丈量下其首尾的宽度,刚好足以让自己趴在上面。
恐惧如同黑潮般淹没了长门的最后一点矜持,圆滚滚的小胖腿不住的打颤,一半是冷,一半则是怕。长门自然认得眼前的物件:所谓的春凳本来是东煌国传入重樱的木器家具,是一种板面宽大,可坐可卧的长凳,可即使在东煌,春凳作为一般家具供人坐卧的时候也并不多见,反而是用来执行家法的用具,东煌向来有‘家法春凳去衣杖责’一说,甚至有志怪轶事说,常年用来执行家法的春凳乃是‘肉红色,甚修润,近抚按之,殆如肉软’,甚至有些说不清的灵性,家里顽劣的女眷光是看见这长凳,臀肉就会一拱一紧,屁股开花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自然就会变得规矩些,东煌的大户人家常喜欢在庭院里摆上这么一条春凳以作警训之用。
至于在重樱是否也已经有了这样的风气,长门并不清楚,但老宫司说过,老旧久用的家具是会变成付丧神的,那也是有灵性的器物,但不管轶事的真假,长门倒真觉得自己身后一对肥润娇臀有些微微的凉意,对刑台的恐惧让她下意识的用手背掩住一瓣臀肉,好像做了错事在家法面前既心虚又委屈的小女孩一样。
站在主殿上居高临下的国人众头目观察着台阶下小女孩胆怯忸怩的动作,应该说不愧是随身散发着贵气的神宫御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胴体却还只是这种程度的害怕,别说只是一个孩子,就算是成年的女子恐怕也会被汹涌的恐惧感压垮才对,但就是这样的气质才有由内而外将其摧毁的乐趣……
随着一阵细碎的洒落声,一把黄澄澄的露金自国人众头目翻覆的掌中滚落台阶,其中几颗不偏不倚的落在长门的脚下,她立刻认出了这些金子,那是三笠大人曾委托她在神宫中秘密铸造的露金,用以在民间流通,令百姓归心,这本是纯度极高的金子,放眼整个重樱都价值连城,但眼下没有任何一人胆敢对这些唾手可得的露金表现出兴趣,在他们看来那是反贼的金子,所谓赃款的金子,就像瘟神一样令人避之不及。
“从神宫里搜出来的露金上每一块都有三笠的押名,此乃如山铁证!你还有什么可争辩?”
国人众头目厉声道
“这么多露金囤积在神宫里,足以证明三笠的党羽在此地根治不浅,往来神宫的香客、巫女、神官必然有不少同党,你现在招出这些人的底细,我们还可以酌情考虑将你移出祸首之列……”
“住口!”
长门突然爆发出来的咆哮声震住了国人众头目的喉舌,幼女的童音就士气的分量来评判竟然毫不逊色于叫阵的武士,长门紧咬着银牙昂首同殿上的国人众忤视,宛如鎏金的双瞳中又好似有火焰在实质的升腾燃烧。
“你这混账、庸人!三笠大人是要开辟亘古伟业的明主!对百姓虚与委蛇的朝臣和幕府才是反贼!我是天钿神宫宫司、天宇受卖命的御神子、也是三笠大人的拥戴,任凭尔等鼠辈再怎么折辱,我也不会出卖主公!”
高亢的童音在主殿庭院的檐柱间回荡彻响,一字一句皆掷地有声,被台阶下浑身赤裸的幼女仅靠呵斥就震慑得噎住了嗓子,国人众头目的脸色由肃穆转为愠怒,胆敢在众人面前挑衅自己威严的女人,台阶下的狐耳幼女还是头一个,但女人终归是女人而已,熬几下屁股板子就能让她重新认识自己的地位了,他手下早已处置过不少性格忠烈的女性,无论是国人贵女亦或是姬武士,在两瓣臀蛋由白转红转紫之前都有一副宁死不屈的士气,不过待剥光衣物捆在春凳上,娇嫩的臀肉在竹板下起伏颤动之后,都只会发出一样的哭嚎而已。
“把她的嘴堵上!即刻行刑!直到这逆贼招供为止!”
恼羞成怒的国人众头目向长门左右的皂隶发号施令,仅凭三句话就决定了长门的命运:在她因熬不住酷刑而开口之前,痛苦都不会结束,没有人再会给她任何礼遇,而保证她不至死的价值也只剩下那份莫须有的供词,除此之外只剩下日复一日煎熬屁股板子的刑罚。
即便是在主殿两旁作为看客的国人众们也于心不忍的摇了摇头,让这么可爱的女孩承受如此凌虐似乎过分残忍了点,但他们的怜香惜玉也就止步于此了,毕竟相比起在乱世中一文不值的同情和善心,接下来他们所能目睹的春色艳景更令人神往,能够将在春凳上熬刑的少女那因痛苦与羞耻而忸怩的雪白胴体尽收眼底,何乐而不为呢?何况仅凭看长门那副小巧可爱又不失丰腴的两片肉臀如何从形似无暇璞玉变得紫红肿烂就不枉在瑟瑟秋风中站上几个时辰。
但血脉偾张的长门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当左右的皂隶抓住她的藕臂向那张即将作为刑台的春凳上押去时候长门依旧没有放弃挣扎,但一个小女孩的力气对掌刑经验丰富的皂隶来说完全是蚍蜉撼树,他们料理过比眼下这个小丫头性格更刚烈的女人,说到底所谓的尊严不过是被肉体凡胎所包裹着的一团精气罢了,施加在肉体上的刑罚会像挤出海绵里浸过的水一样将她们的尊严和矜持榨尽。
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在空旷的主殿间回响,皂隶的巴掌狠狠的抽打在了长门的右半边屁股蛋上,新伤覆上旧伤,之前经过土一揆责打而染上了淡淡桃色的臀瓣清晰的烙上了五指的痕迹,那种精准的、不留余力的、专门为了对付女人的娇臀而练习的掌法完全不似之前挨打时那般疼得毫无章法,皂隶的巴掌像是将疼痛两个字生生嵌入腠理,巴掌所能覆盖的面积每一寸都是仿佛经受灼烧,又用烈酒加以淬炼般的疼,长门能够清晰的感觉到自己挨了巴掌的那瓣臀在带着凉意的空气中发热肿胀,伴随着疼痛席卷而来的则是经受折辱后的羞耻和愠怒,臀肉上的痛楚令长门的理智涣散,她想用指甲去抓、用牙齿去咬、在发现自己纵使拼尽全力去挣扎也无济于事后只能放声咆哮。
“好疼!……鼠辈,你们怎么敢……嗯唔!”
一连串的咒骂尚未脱口便被竹筒制成的口枷堵在了嘴里,那东西是被身后的皂隶趁自己张嘴的时候塞进嘴里的,如同马匹的嚼子一般横在自己上下两排牙齿之间,通过捆扎在自己脑后的绳子来勒紧固定,正如同所有第一次被套上缰绳的牲畜一样,长门那双几近决眦的双眸里除了错愕与愤怒之外更多的是恐惧和绝望,除了发出如同抽泣般的呜咽声音之外她现在连完整的说出一句话都做不到,别说反抗,即便她现在想通过供认罪行的方式逃避酷刑都做不到,也知道这个时候长门才意识到残忍的事实,自己的供词对国人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失去了三笠的庇护和神宫宫司的身份,她早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只要他们想,可以处于任何理由践踏蹂躏自己。
尽管因为预料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而失去了挣扎的动力,被拖拽向处刑台的过程也顺利了不少,但当小腹和胸前的小浆果接触到早已被瑟瑟秋风吹袭得冰凉渗人的春凳时还是下意识的弹起身体,但这种微弱的抗拒动作很快就被皂隶用手重新按下,分别向前后并拢的手脚也被绳索一并固定,这样的姿势自然谈不上舒服,但本身也并不是一种折磨,为了防止受刑的女犯因为过度挣扎而磨破手脚,捆绑四肢的声索刻意用了质地柔和的棉绳,这样的仁慈对现在如同案板鱼肉的长门来说显得格外讽刺,就连轻轻扭动下腰肢试图试探下自己能够活动的空间也被皂隶呵斥着老实下来。
长门从被竹枷堵塞的嘴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声,在冰凉春凳上忸怩的胴体也平复下来,凭眼下的境遇,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甚至会进一步激起掌刑者的施虐欲,长门自己身为神宫的宫司,因职责之故也曾在主殿的石阶尽头高高在上的监刑,多半是处罚一些私自盗用神宫钱款或是触犯戒律的巫女,每每有新晋的巫女初来乍到,这样的惩戒隔三差五就会上演一遍,但无论熬过多少次屁股板子,巫女们被被绑上春凳的时候还是会嚎啕大哭,往往是哭得越大声,落下的板子便更加狠戾,神宫的刑具是蔑片制的,轻便且结实,是最省力气又最让屁股难熬的刑具,往往是蔑片砸在臀肉上炸裂的脆生肉响与受刑者的哭声交织在一切,被迫在一旁跪坐观刑的巫女们眼看着同僚的屁股从白嫩的璞玉变成肿烂的桃国,难免心有余悸的揉起自己的屁股来,往往是打到最后,表层的皮肉皆被尽数打的松散,每一板下去发出的便是蔑片与臀上烂肉的粘连之音,就连长门自己都心中发怵。
不知是不是天宇受卖命刻意要作弄虔徒来历练她们的意志,如今要对自己施刑的皂隶手上所拿的正是神宫之前惩戒巫女所用的蔑片板子,长门闭上眼睛将脑袋埋低,这样即便疼得掉泪也不会被轻易的察觉,她下意识的五指攥拳,让臀肉尽可能的绷紧,只待那凶狠的刑具击破空气,落在自己裸臀上。
约莫几次呼吸的时间,长门感觉空气粘稠的像糖稀一般,她的吐纳因恐惧而变得凝重,当她准备再呼出一口气来平复心跳的时候,耳畔忽然传来可怕的呼啸声,其势之快长门几乎来不及反应…
“啪!——”
蔑片精准的落在长门的左半边屁股上,炸裂似的脆响余音荡出数十米开外,遭到板子打击的那片臀肉肉眼可见的凹陷下去,待蔑片抬起时赫然印上一片板花,较另一瓣屁股蛋已然肿起些许;对长门来说,刚才的一击则像是被暴起的毒蛇很咬了一口,几乎要崩断肌肉的痛楚仿佛顺着筋骨的脉络蔓延至自己的四肢百骸,蔑片薄而韧,打在屁股上造成的痛楚是如同鞭子般清晰的锐痛,她几乎是跟着自己屁股的肉响一同喊了出来,长门的脑子里只剩下一条讯息,那就是这般如同在地狱里受劫的痛苦还会接二连三的落在自己屁股上,但几乎来不及绝望,第二板便趁上一板抬起的罅隙也带着劲风落下……
“啪!——”
“啪!——”
“啪!——”
接下来左右开弓的三板子长门几乎是在失神的状态下硬扛过去,她身体里最后一点维持尊严的理智都已经被蔑片的责打挤了出去,只能拼尽全力的嚎啕大哭,希望哭喊能让屁股上的疼痛有所缓解,可直到嗓子都变得喑哑,口水从口枷的缝隙间不住的淌在春凳上,两片臀肉的煎熬都未曾减弱半分,渐渐地长门已经感受不到皮肉的疼痛了,卯足力气的四板下去她的两瓣臀肉就已经变得红肿不堪,表层只剩下火辣辣的灼痛,真正难熬的是腠理的筋脉,每一板都将疼痛打进了肉里,但每一板结束都会在皮肉下留下又痒又麻的余震,令即便是板子交替的间隙间也无比的煎熬。
皂隶对打击面的把握相当精准,每一次落板的位置都与上一次相差无几,因此长门的屁股上并未出现错落的板花,而是两片规则的矩形肿痕向四周扩散,每一板下去再抬起,屁股蛋的颜色都与之前不同,一次比一次红的深邃通透,从最开始似微施脂粉的红润,到仿佛成熟果实般的大片晕染,长门的屁股早已经看不见一点肉色,周遭观刑的国人众们倒是饱了眼福,他们已经见过不少丰腴肥臀落得肿烂淤紫的下场,长门这样的幼女娇臀虽然不似那些风韵正茂的女人一样会掀起养眼的臀浪,却更显得玲珑可爱,反而让人期待她被蹂躏的模样。
“啪!——”
板声再度破空,长门只觉得自己的屁股肯定已经被砸了个稀烂,虽然她还是没有放弃顽抗到底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小女孩的脆弱却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因忍痛而蜷缩起来的脚趾和朦胧的泪眼让铁石人也难免心生怜悯。
“呜呜……咕呜……!”
待第十下板子落在已经泛起紫砂的娇臀上,长门的体力所能及只剩下对疼痛做出反应的痉挛,像上钩的鱼儿一样扑腾着身体,即便是这样的挣扎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似乎是察觉到了长门的耐受已经达到了极限,两个皂隶放下了刑具,将手搭在长门滚烫且肿胀的臀肉上揉搓起来以便消肿,眼下并没有多少药品可以用来给这丫头智商,如果真把她的屁股打到血肉模糊,感染是很麻烦的问题,如今长门作为玩物的价值之一便是要耐用才行。
之前的哭喊已经消耗了长门的不少体力,慢慢恢复知觉的臀肉感受到两只手掌正把玩揉搓着自己的屁股,至少还没有完全被打烂就已经值得庆幸,从之前紧绷的状态中忽然解脱的长门只觉得浑身的肌肉都松弛了下去,臀肉上的肿块被慢慢的揉搓消解,冰凉的巴掌接触到滚烫的红臀产生的奇妙反应甚至让长门觉得有些舒服,就连呻吟都不知不觉变得妩媚起来,长门感受着自己饱受摧残的身体慢慢放松下去,紧接着便是股间的一股暖流……
“这丫头居然被打尿吗?”
“听她那叫声,果然这些女人都是一样的贱骨头……”
尖锐刻薄的议论让长门也注意到了自己失禁的事实,似乎是为了惩罚她在受刑过程中排泄的丑态,皂隶一巴掌打在了长门刚刚有些消肿的娇臀上,引来的又是长门的一声娇呼,长门不再有抗拒的动作,她的身体已经酥麻的好像躺在云朵上一般,在含糊的几声呜咽之后,长门只觉得自己的视野变得越来越暗,四周的声音也愈发清晰起来,身体则变得沉重……
两旁的皂隶见春凳上的女孩没了反应,在掐了几下屁股又探查鼻息之后便确认了长门确实已经昏厥过去。
有些声音仍能传入长门的耳朵里,但她早已难以辨析那些话的意义……